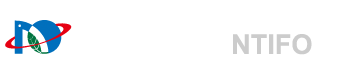395期-【原農永續力】一個看待原住民食物生產知識的觀點

#一個看待原住民食物生產知識的觀點
撰文、圖片提供——張瑋琦
2024年起在《農訓雜誌》的邀請下,我轉換跑道執筆新專欄──原農永續力,本專欄介紹台灣原住民族傳統食物生產知識中所蘊含的永續智慧。
我使用「食物生產」一詞代替「農業」,是因為農業具有產業的意涵,而原住民族的傳統食物生產──農耕、狩獵、漁獵、採集或畜牧,並非全然屬於經濟活動,尚具有維生、饋贈、宗教信仰需求或以物易物等多重功能。
反思現代主義
現代主義的經濟發展最大的問題即在於一昧追求 GNP(國民生產毛額)成長,認為「不發展」、「經濟不成長」就等於貧窮與不幸,「成長做為意識型態」已是現代化社會的通病。
以「成長」(growth )為目標的發展並未將自然資本納入考慮,經常忽視地球資源有限的現實,不斷擴張經濟體的結果,導致溫室效應、臭氧層破壞等問題。
現代主義的科技發展則以追求「穩定」的生產能力為目標,重視功能的效率性,透過內部控制,快速修正(消滅)外部的影響因素,將維持自己利益的恆定視為「平衡」。抱持此一思維者對生態系產生兩種極端的誤判,一是把生態系視為連續的、內在平衡的、具有自我修復力的客體,認為只要減少人為干預,就能維持或恢復平衡。這種見解常見於極端的保育主義者,例如:將原住民驅逐出傳統領域,劃定國家公園的做法;或八八風災後主張「讓山林回歸大自然」,而強迫原住民集體遷村的政策。
另一種誤判則是將生態系視為混亂的、蠻荒的、不穩定的客體,因此必須發展預測與控制技術,透過征服及利用自然來改善自己的生活。這種見解常見於極端的科學主義者,例如:以基因編輯或改造來解決育種的「不確定性」;或期待科學家及工程師能一勞永逸地解決氣候變遷問題。上述兩種誤判都源自於將生態系視為客體,而建立起文化 v.s. 自然、人類 v.s. 非人類的二元對立宇宙觀。
受制於現代主義的經濟發展觀與科技發展觀,當代人在尋找環境問題的解方時,不斷落入「環境保育與經濟發展兩難」的矛盾爭執中。要解決此一矛盾必須擺脫發展等於成長的謬誤公式,並打破將生態系視為客體的二元對立宇宙觀。
原住民族生態知識
原住民族生態知識,是一套與西方現代化論點下所構築的知識論不同的知識系統。過去在西方強勢的殖民下,原住民族生態知識的價值全然遭受否定。
原住民族生態知識與西方知識最大的差別,在於不採取二元對立的宇宙觀,「自然」與「文化」不是分開的,「人」與「非人類物種」也不是對立的。世界許多原住民族認為自己與大自然是一體的,動物與自己是手足或具有親緣關係。
原住民知識反應了特定地區住民對其自身與其自然環境的動態關係的了解,以及他們組織動植物、文化信仰和歷史的知識來提升其生活的方式 。尊重地球,與地球和諧平衡地生活做為生存的必要條件,是世界各地原住民(包含台灣原住民)宇宙觀的基本原則。
傳統原住民的宇宙觀、自然法則與慣習法是一體的,例如:泰雅族的 Gaya(祖訓),規範了族人祭儀、農耕、狩獵、人際互動的法則,並定義了人與森林和流域的關係。阿美族是台灣原住民各族中採集野菜知識最為豐富的民族,他們不但愛吃野菜,甚至用野菜來承載其宇宙觀和我族觀。飛魚是達悟族重要的食物,為了保護飛魚的資源永續,他們建構了一套祭飛魚、捕飛魚和吃飛魚的生態文化體系。豆類是布農族重要的蛋白質來源,從他們的「豆知識」可探知人與動物的關係,以及土地利用的智慧。

如何看待原住民族生態知識
2019 年,巴黎學派著名的哲學家、人類學家與社會學家布魯諾.拉圖在《面對蓋婭:新氣候體制八講》中指出:「我們應該探索多元的表達方式,聽到所有非人類物種的聲音,為其代言」。
當代許多研究者嘗試將原住民知識抽離出來放入科學的架構來驗證,我認為這樣的做法並非真正肯認原住民知識的價值,只是把原住民知識當成另外一種資訊加到科學知識中,而沒有去挑戰科學知識的預設。也有些研究者把原住民知識簡化成「過去的文化遺產」,以「保存」的方法來看待它,我認為這只是一種基於發展論述的膚淺概念,或殖民者高高在上的俯視視角。
我認為必須反思現代主義對於「單一世界觀」及「單一生活方式」的文化霸權假設,才能真正肯認原住民知識的實踐。
基於上述論點,本專欄不希望把原住民族知識當成奇風異俗來介紹,而是希望帶大家認識原住民的食物生產與生態互動的方式,以及當代原住民如何鑑古知新回應社會變遷的時代性價值。透過這個專欄,願與讀者一起反思深植在我們心中的現代主義發展觀,學習多元的永續農業新典範。